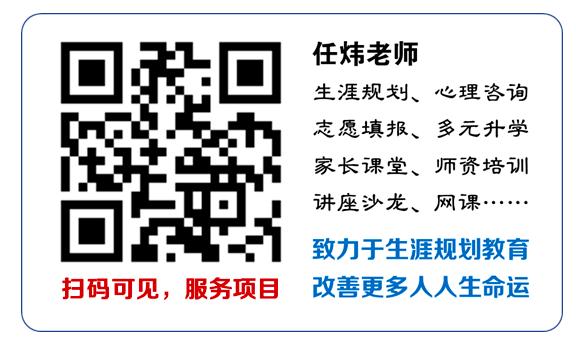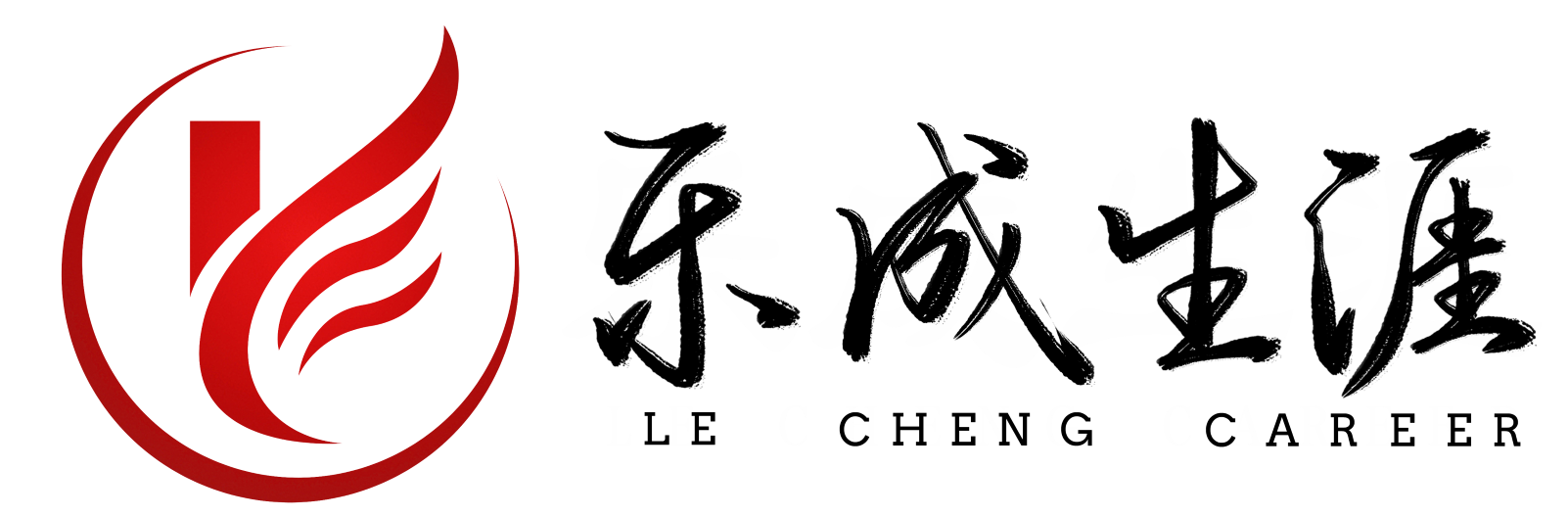2000.10.1
国庆,奥运也闭幕。除了电视节目多了点花样,与我们没什么影响。几个同学兴致倒好,外出买了些穿的。
我无心外出,上午看书,中午吃饭,下棋,然后一下午时间写了四封信,效率够低的。不过无所谓,要的就那感觉,都是给同龄人的信。
尽管学习上已处于停滞阶段,却无心给北京的师哥师姐求教,不耻上问也是件难事啊!
晚,下棋看电视,闲适之极。
10.3
又迷茫了,在考研与回家乡县中当教师之间犹疑。
人的一生该怎么过,又一次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当感觉又困又饿时,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思考,抄起书便离开了教室。我还要想!
昨去空工院,热情的老乡要带我上白鹿原,可路太稀便半道而返。
晚与小妹通话(昨是她生日),得知家里人不把她生日当一回事儿,她心里有老大的不满意,但接到我的电话她很高兴(其实还是她以前提醒我的呢!)我说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她却仍是高兴——似乎只要我记得她就满足了,到底是孩子,单纯又可爱。
上了第二回通宵网,本与**约好聊天,却整晚没找到她(后来才知,阴差阳错地我记错了她的号)。今天电话里,她连说恨死我了,我又无言以对,当然挂电话时还是皆大欢喜的。
午体后,精神恢复。吃过晚饭开读《爱弥儿Ⅱ》,竟爱不释手。到晚教室快熄灯时读毕。补记:抽完第二包烟,用了十天。头一包是二十天。
10.4
(晨,在床上)一个念头强烈地攫住我心——回家乡的母校做教师。我一直坚信人一生最大的幸事是做自己喜欢做并适合做的事。难道,我的使命就是这?!
为何现在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考研的局势紧张是一个原因(是直接而不是主要原因),也就是在昨晚的网上感受到这一点的,太多的人去争考心理系而又不知自己要干什么(我也因此开始反省自己考研的动机);学心理的也是迷茫(从他们发表的文字来看)……
当然,平心而论,我并非是害怕竞争,而是厌恶竞争。看着人们你推我攘或是摩肩接踵地走在一路上,我就不愿走这条路了。
好在我看重的是精神生活,物质方面无所谓,因而不是必须得参与那种竞争。
现在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找并巩固(坚定)今生的信仰(理想)还要读些书,包括卢梭的《怀悔录》。
10.5
昨日买到《忏悔录》等一批书,还去了新开的西安国书大厦.《忏》今日读毕。
10.6.晚看碟《阳光灿烂的日子》,觉得米兰形象挺不错。能看到这样的片子,丰富了感受,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上午还是考虑定居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哩,倾向于认为自己在两者中生活几无差别。现在看来,大城市信息的丰富和快捷是须加以考虑的,我的天性不适合单调闲塞的生活,而向往丰富动态的生活。
还有,下午去***处,见其宿舍自配了电脑且通天有电,生活丰富方便了许多,想人应尽力向好处发展的,保守的自给自足思想不但于己,于社会亦无利。
即使为人师表,知足常乐的生活原则也不该带给学生们。人,就应该积极进取,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不能因满足而止步不前。
10.7
读王朔,从文集到《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看他和老侠那么痛快淋漓地评价别人(对余杰批得相当狂,我觉得也妥切,有同感),倒不好说他了。无论说什么,我知道都嫌嫩的。
晚归,在园子里与*从尼采谈到人生哲学再到老庄,他推崇后者,我说不可将信仰普遍化,不可推己及人,我知道我和他知道的都太少。
10.8
补记。昨日上午者了影碟《第六感》,确感其“震撼效果”。
今读完《美人赠我蒙汗药》,有点寒心加恶心,不是针对王朔,而是针对那个明明是主要发言者不学无术乱点江山批评别人大言不惭无信仰无文化根基满肚子愤世嫉俗整个心虚荣空虚跳梁小丑吠日蜀犬样的“第二作者”,其实他的话多半都可用来形容他自己。
我当然对其花枪套路已见多不怪,不气愤也不同情,故不屑一顾以节省感情,免中圈套使其小人得志——他的目的还不就是想让自己出名,只要能在人民大众心中占住一席之地,才不管是什么形象呢。因此不管视其为一反文化斗士还是一无知小儿还是疯语狂人。
唉,有这帮文丐在,文坛何得安宁,社会何得清静?故而寒心。
当然,对于个人来说,尚可自救,社会如何实行集体自救,有待考虑(不过,她对余杰的评价倒还击中要害)7日补。
顺便说说王朔,我认为这个人基本还是好的,写的小说无非就是疯子给傻子看的东西,只要人不是真傻,倒不致被他那两下子花枪晃晕,仍可在一笑之后保持清醒,不必抱过高希望,他的东西当相声小品看还是可以的,至于他的做人处世,无须了解更不必效仿,这个人倒还有自知之明,对不太知道的事或人不乱说话,不像老侠之辈,动不动就拿名人大家开刀,其实肚里没货——他倒真他*有勇气说!
晚,与**谈,主动的,也巧,想找到她还真如愿了。谈确实使我有释然感,但她的话不够平白轻松,我觉得很难交流。
回宿舍途中,我总结了一句:“也许每个人都有一张面对人生(“实则生活”)的(隐藏于表面的脸下的)脸,你那张是比较严肃的,我的呢,带着微笑,还视之为两人差别的表现之一。
我事先在文章中称她为“知己”,当问我算不算她的知己时,她犹疑了一下,说“算也不算”。我们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
10.9
如果一个人,叫他立即去死,他眉都不皱一下,这是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我现在就是这样,刚在隔壁宿舍神吹闲侃了一番,特别痛快,想生活原是可以那么简单有趣的,只要顺着自己的性情,少去功利心;而在这之前,我在园子里徘徊好久,考虑将来,没有结果。
10.10
在发给**的信中,表达了做教师而不做学者的打算,实际考虑为:先做几年中学教师(一为丰富生活感受——如今的学习动力,效率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做学生,只知学习,不知生活引起的,二为“还愿”——我要到家乡中学去,如果不去会不踏实的。尽管未向任何人许愿回母校,但发现自己的情感已深深地固结在那里。回去教书,舍此别无地途),然后考研到北京。
信是带着近乎冲动的情绪写的(其对内心正经历考研还是不考的冲突,焦虑感蒙蔽了理智,故易走极端,考虑问题难以周全),昨天写好后,也觉有些冒失,故未急发,今天重读(本打算重拟一封,却没成功,因为找不到那种一泻千里的激情了),见信中已讲清所言非定论,故最终也是投寄出去,而其时已发觉说自己“不适合做学者”不妥,因为实际情况是,现在的我若直接向学者道路进发是不宜的,一目的不明确,二对专业已失兴趣,无法保证将来不会卷土重来。
以后不能轻易预言一辈子的事了。
10.11
下午与**谈话中透露了毕业后回家乡当教师的打算。其实,自知想法还不够成熟,还需时间考虑。
作于2000年大三期间
添加任炜老师微信